|
饶雨SEO博客 https://www.raoyu.net 在九月,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学校都将陆续以各种方式开学,在假期中沉寂的校园,也随之恢复读书声、讲课声,还有学生们的交谈声。而在阿富汗,自上个月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重新掌权后,女学生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女大学生开学情况,也在这个月初再度受到各界关注。 据“我们视频”“四川观察”等媒体转引海外报道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教育部门目前颁发规定,在私立大学就读的女性必须穿着长袍、佩戴面纱,男女必须分开上课,或者至少用帘子隔开。部分私立大学的复课指南显示,将开始为女生单独上课做准备。受制于女性教师数量少、教室资源缺乏等,在暂时无法分开上课的学校,男生和女生分别坐在教室的两侧,中间有不透明的帘子分隔。塔利班高级官员称,教室用布帘隔开“完全可以接受”。 9月7日,“我们视频“世面栏目报道画面。 这是塔利班第二次掌权,在进入首都喀布尔后,塔利班通过新闻发布会等方式数次表示,将保障女性的上学和工作权利。人们担心塔利班像首次掌权期间一样,禁止女性进入大学。如今到了开学季,女性已经被允许进入大学继续接受教育。这是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地方。不过,女性与男性分开上课的规定和画面使人看到,阿富汗女性的平等教育权利之路依然困难重重,充满不确定性。而即便在塔利班此次重新执政前,在阿富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也普遍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没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在塔利班之外,对女性处境影响更为日常的性别等级观念。长久以来,它几乎已经渗入到每个角落。在过去十几年有过一些改变,却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在八月中旬,大量阿富汗人涌入机场,拥挤的人群中也极少能见到女性。 动画片《养家之人》(The Breadwinner 2017)剧照。 作为远方的人,我们或许唯有了解阿富汗女性的过去,了解她们在上学、工作、衣着和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处境,才可能对她们的恐惧和追求多一点理解。我们无法对她们产生“现场感”,那些展开描写和反思的书籍则成为一种思考资源。本文鉴于此,基于小说、非虚构和回忆录等文本,向书友们呈现书籍中的阿富汗女性,看见她们的生活,以及对知识、艺术等精神世界的渴望,对工作的追求。她们在此努力,也在此自我救赎。 撰文 | 帕孜丽娅 01 婚姻:一段无关浪漫的关系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这是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灿烂千阳》中的句子。 《灿烂千阳》,[美] 卡勒德·胡赛尼 著,李继宏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07年9月。 《灿烂千阳》以两名女性在阿富汗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中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历史车轮之下,阿富汗普通人、普通女性最有可能的命运。主人公玛丽雅姆和莱拉共事一夫,但在这段家庭关系中,两人更像姐妹、母女,甚至是精神共同体。 玛丽雅姆是当地富商和女仆的私生女,儿时的她并不明白“私生女”在阿富汗意味着什么,直到十五岁那年母亲突然离世,她在被父亲和他的三位妻子嫁给远在喀布尔的四十多岁的鞋匠拉希德时才知道,一个不被认可的孩子,尤其是一个女孩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这场婚姻的开始犹如一场风暴,卷走了玛丽雅姆所有的纯真与美好。往后的日子,她是在无休止的家暴中度过的。而丈夫的殴打带来的则是六次流产和往后的不孕。在确定玛丽雅姆再也无法生出孩子后,拉希德的目光转向了因战争失去了家人、被恋人抛弃的少女莱拉。命运的无常和拉希德的欺骗,让莱拉成为了拉希德的第二任妻子。 至此,两个女人一同承担着这个家庭的贫穷、暴力和外界无休止的战乱,互相陪伴、互相支撑,甚至用生命保护着彼此。在拉希德想要掐死莱拉时,是玛丽雅姆愤而反抗,杀死拉希德,解救了莱拉,这才让莱拉有了后来的新生活——虽然这让玛丽雅姆献出了生命。 “在这最后一刻,玛丽雅姆燃起了这么多希望。然而,当她闭上双眼,她心中再也没有懊悔,而是充满了一阵安宁的感觉。她想到她进入这个世界的身份,一个低贱的乡下人所生的哈拉米,一件人们不想要的东西,一次可怜的、后悔莫及的事故。一棵杂草。然而,当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是一个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的女人。她以朋友、同伴、监护人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以母亲的身份。她终究成了别人眼中的重要人物。不。这样死去并不算糟糕,玛丽雅姆想。不算太糟糕。对于一段开头不合法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合法的结局。” 在被执行枪决前,早就心如死水的玛丽雅姆再次感受到了希望,而这份希望是她的精神寄托者莱拉赋予她的,只要莱拉实现了她曾渴求过的有爱与和平的生活,她就满足了。 在阿富汗,依然有许多人遵循一夫多妻的原则,虽然依照宗教丈夫娶新妻子前需获得原配的同意,但在现实当中,妻子向来是默默遵从丈夫的决定。 在中国摄影师、作者原老未的《罩袍之刺》一书中,也曾讲述一夫多妻的生活里,面对迎娶新娘的丈夫,毫无反抗之力的妻子。 《罩袍之刺》,原老未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 穷人家的碧碧结婚四年后终于有了身孕,结果接连生下的都是女儿,至此,她知道早就看她不顺眼的丈夫一定会再娶。果不其然,2008年,碧碧36岁的丈夫迎娶了一位16岁的新娘,碧碧在法律意义上多了一个亲人。 这个新娘很快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而碧碧和女儿们,则被赶到家中走廊,再也不许她们进入正屋。后来,阿富汗局势愈发紧张,碧碧的丈夫决定带全家逃至伊朗,只是这个全家里不包括碧碧和她的孩子。丈夫离开前,甚至命令碧碧不得趁着他不在时进入房间,否则只要被他发现,定会打折她的腿。 后来,碧碧因寒冷、过度疲惫晕倒,人们送她去医院后才知道她的子宫内长了直径11厘米的肿瘤。但3万阿富汗尼的手术费用对碧碧而言是个天文数字,她只能随便买些药顶着,以忍受病痛。 “碧碧很像一个溺水的人,她的双臂也曾努力挥舞过,可呼救时更多的水倒灌进她的喉咙,碧碧隐隐感到外国人也许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但她没劲儿伸手,对于回到岸上已再无斗志。” 当然,并不是每一场婚姻都是悲剧,在阿富汗依然有不少女性能够嫁给温厚善良的丈夫,度过还算安稳的家庭生活。只是在道德至上的阿富汗,未婚男女绝不能私自见面,谈情说爱、私定终身更是违反法律,大多数人第一次见自己的妻子和丈夫是在婚礼中。 为了保证姻亲双方彼此熟悉了解,也为了更好地沟通嫁妆彩礼问题,许多阿富汗人都会选择与家族内部的人结婚,男的娶表亲,女的嫁堂哥,再常见不过。正如阿富汗的那句古谚:近亲结婚是上天的旨意。遵循古老而传统的社会观念的阿富汗人,相信一切的安排都有上天的用意,婚姻是否幸福、丈夫是否殴打妻子,一切自有天定,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默默承受属于自己的命运。 02 衣着:规训之外的天性 茶达里,尤其是蓝色的茶达里,似乎是阿富汗女人身上最引人瞩目的“标签”。但在早期的阿富汗,这种只在眼部缝有细密网格的长袍其实是上流社会中女眷的穿着。 随着越来越多人模仿上流社会的穿着,茶达里也开始广泛流行。尤其是在保守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人们坚信正经的女人会身着茶达里,避免她的容貌被别的男人瞧见。再后来,阿富汗内战不休,越来越多女性选择穿上茶达里,以保护自己不受侵犯。 茶达里成为阿富汗所有女性必须穿的服饰,则是在塔利班首次统治时期。在1996年至2001年间,衣着规定包括:在没有男性陪伴的情况下,女性禁止单独出门;女性出门必须严格穿戴布卡,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体,不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女性禁止工作;女童除了在12岁前可进入教授古兰经的学校上学外,不能再接受其他教育等。 此后,那些未曾养成蒙面习惯的女孩也不得不穿上茶达里,将自己的身体掩藏在蓝色的长袍里。 阿富汗唯一一位女性国会议员法齐娅·库菲曾在《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中写下自己第一次穿上茶达里的心情: “透过蓝色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包围。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变大的同时也变小了许多。在厚厚的蒙面长袍之下,我的呼吸喘息声儿变得很响,身子也越来越热,仿佛就要得幽闭恐惧症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块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小了,不重要了,孤立无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曾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突然又关闭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派对——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丝毫意义。”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阿富汗] 法齐娅·库菲 著,章忠建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0月。 2001年后,女性拥有了脱掉茶达里的权利。虽然在这之后,依然有很多阿富汗女性习惯于日常穿着茶达里,但茶达里只是起到了隔绝女性身体的作用,女性内心对自由与美的向往并未停歇。此前,女性被禁止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此后,热爱唱歌、跳舞的阿富汗女性也重新拾起天性,在没有男人在场的时候,她们会聚在一起关上院门,伴着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一起跳舞。 《罩袍之刺》中的第一个主人公古尔赞婶婶的院子就是供周围的女人放心跳舞的地方。 古尔赞婶婶的女儿纳吉亚和里诺创办了巴达赫尚的第一家女性广播电台,里诺主持的《卓也什》(达利语,意指燃烧着)是全省收听率最高的点歌栏目。巴达赫尚是阿富汗最贫穷的省份之一,这里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国内的排名同样垫底,但这里的女人对点歌却格外有热情,给电台打电话播放自己选择的歌曲是她们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快乐。即便每一次点歌都要小心翼翼,深怕说太多话被婆婆责骂浪费电话费。 纪录片《阿富汗明星》(Afghan Star 2009)画面。 而对更大城市的女性而言,更大的快乐来自美丽的衣服、高跟鞋和能让她们变得更美的美容院。就这一点,她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性并无不同。 2002年初,喀布尔的街头逐渐出现了美容院,这个只为女性服务的神秘场所对女性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临街的深色反光玻璃,门板上贴满的浓妆艳抹的伊朗女人的巨幅海报,穿着低胸小背心的美容师和摘下头巾露出各色秀发的顾客,这些是城市中最独特的风景线。 “在这里她们可以摘下头巾,让美容师为她们洁面、绞脸。新娘妆会把原本又粗又黑的眉毛画得高挑而夸张,再根据婚礼礼服颜色(通常是绿色),在眼皮抹上各种颜色的眼影。很多新娘还喜欢在脸上贴水钻,在高耸的发髻上撒亮晶晶的银色粉末也很流行。”也许对她们而言,当爱美的本能被压抑后,反而用一种更夺目的方式出现了。 03 上学、工作:勇气与梦想 “在阿富汗,一个新生的女孩听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接生现场的人们对她母亲说的安慰话:‘是个女儿。可怜的女儿。’” 这是法齐娅在《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中写给她两个女儿的信里的句子。 纪录片《阿富汗:没有结束的战争》(Afghanistan: War without End 2011)画面。 阿富汗的女孩子很难有属于自己的决定权,上学、去工作挣钱,这些在男孩子身上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女孩子身上总是很难实现。在这里,一个女孩唯一的前途是嫁人,上学的女孩也很难出去工作赚钱养家,所以没有经济价值的她们,无需去接受教育。更重要的是,很多阿富汗人相信,念了书的女孩很容易产生疑问,而疑问会让这里的男人不适、愤怒甚至恐惧,既然她们终究要嫁人,就不需要去冒会让未来丈夫不适的风险。因此,阿富汗女性的文盲比率极高,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只有一本《古兰经》。 不过很多阿富汗母亲并不反对自己的女儿接受教育,她们甚至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女儿去学习,这样也许女儿就有可能当上医生或者老师,过上和她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所以法齐娅的妈妈在丈夫死后,得知女儿想要读书的心愿,二话没说就同意将女儿送进学校;古尔赞婶婶自己只读到了小学,但是她让两个女儿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但到了塔利班首次当权时期,女校的学生被赶回家,女性的教育和工作一度中断,就读医学专业的法齐娅的医生梦也就此落空。女性失去了受教育权,也不被允许出去工作,因为一个懂事、有道德的女人是守在家中的顺从的女人,而那些企图出去抛头露面的,被认为是不过“是想勾引男人的不正经女人”罢了。 延伸阅读:《陌生的阿富汗》,班卓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 在2001年后,女校曾重新开始接收女学生,而那些贫穷的家庭,也不得不接受妻子外出赚些生活费,在家里看来,反正以她们的年纪,已经没有哪个男人会看得上了。 《罩袍之刺》中的女子大多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馕铺的古尔赞婶婶、武术老师卡瓦利、残疾画家鲁巴巴都在用自己的劳动赚取报酬,贴补家用乃至养活整个家庭。 出生于坎大哈的美国商人瑞吉娜·哈米迪的绣坊“坎大哈珍宝”中,就有大量的全职和兼职女性员工。其中有一位元老级绣工莎克拉,在这个绣坊工作了14年,从21岁时的兼职女工到35岁的“高龄”绣工,她在工作中获得了比婚姻更多的安全感和成就感。 莎克拉没上过学,却在算术方面极有天赋,因此自小跟着父亲一起做买卖。后来经历了苏联入侵、塔利班统治等时期,莎克拉对童年的印象并不深刻,只觉得搬到坎大哈没多久,塔利班就出现了。按照塔利班的规定,女性只能在直系男性亲属的陪同下出门,因此,在那之后的10年里,包括塔利班下台后的头两年,莎克拉都没有去过离家一公里的地方。她的日常就是帮母亲做家务,之后就开始做绣工。长年累月,莎克拉的手艺极为精湛。 女老板瑞吉娜看重莎克拉的手艺,也看出了常年在家的莎克拉的抑郁和不快乐,于是答应给她最高的月薪,让她去绣坊全职工作。此后的十多年,莎克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绣坊度过的。她不想结婚,也明白以自己35岁的“高龄”不会有合适的未婚男人愿意娶她为妻,与其嫁给一个丧偶的穷老汉,去冒被殴打、当奴隶一样使唤的风险,莎克拉更愿意像现在一样生活。 她是全家收入最高的人,这也让她说的每一句话在家庭举足轻重,她有钱,因此可以为自己作任何决定,而家中的每个人也都尊重她的决定。 “‘如果我没钱没工作,所有人都可以对我发号施令。现在,他们已当我是个男人。’在如今的阿富汗,是个男人是对女人的一种恭维。” “你问我从坎大哈珍宝得到了什么?勇气。曾经的我很胆小,不敢自己出门,也不敢和别人说话。但现在我敢去任何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即使让我出国,我也无所畏惧。” 延伸阅读:《无规则游戏》,[美] 塔米姆·安萨利 著,钟鹰翔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 04 祖国:离开的和留下的 无休止的战乱让许多人选择离开阿富汗,选择去邻近的巴基斯坦、伊朗甚至更遥远的美国生活。但一种故国情怀一直牵引着很多阿富汗人,让他们在离开后,再度回到故国,选择与自己的国家共同面对未来的一切,即便那可能意味着数不清的爆炸与死亡。 阿富汗的女性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也许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她们早就厌倦了战争,厌倦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但另一方面,她们又无法完全割舍这片土地。 《灿烂千阳》中的玛丽雅姆和莱拉在某种意义上是精神共同体,她们的感受可能代表了许许多多阿富汗女性内心的复杂情绪。 “一年年秋去冬又来,几个总统在喀布尔上任又被谋杀;一个帝国入侵阿富汗又被打败,旧的战争才结束新的战争又开始。但玛丽雅姆从没留意,从不关心。她躲在自己心灵的一个遥远角落,独自度过了这些岁月。那儿是一片干旱贫瘠的土地,没有希望,也没有哀伤;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那儿无所谓未来。那儿的过去只留下这个教训:爱是使人遍体鳞伤的错误,而它的帮凶,希望,则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无论什么时候,若这一对剧毒的两生花开始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玛丽雅姆就会将它们连根拔除。她把它们拔起来,还没拿稳就赶紧将其掩埋。” 玛丽雅姆的生活如同一潭死水,她仿佛早就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爱,但最后,她在借由莱拉的身体离开阿富汗开始新生活后,又选择回到故国,参与这里的建设。 “玛丽雅姆离得并不遥远。她就在这儿,在这些他们重新粉刷过的墙壁之中,在他们种下的那些树苗之中,在那些给孩子保暖的毛毯之中,在那些枕头、书本和铅笔之中。她就在孩子们的笑声之中。她就在阿兹莎背诵的诗句和她朝西方鞠躬时念出的经文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玛丽雅姆就在莱拉自己心中,在那儿,她发出一千个太阳般灿烂的光芒。” 如果说玛丽雅姆和莱拉的故事是小说,那《罩袍之刺》中的小女孩热扎伊与商人瑞吉娜的坚持,则是一种更为真切的人生选择。 热扎伊的父母从阿富汗逃难去了伊朗的扎黑丹,热扎伊出生在那里。扎黑丹有大量阿富汗难民,但热扎伊一家并不住在阿富汗居民区,他们的邻居都是当地的伊朗人。一次与邻居男孩的争吵让热扎伊得知自己与那些人不一样,她是阿富汗人,体内流的是阿富汗人的血液。 在得知自己的身份后,热扎伊对伊朗有了全身心的抗拒,直到12岁那年生日,被父亲问及生日礼物时,热扎伊说,她什么都不要,只想回到阿富汗,即便那里再穷再苦,她也愿意回到那里,尽全力使它变好。 13岁那年,热扎伊终于实现了心愿,回到了那片朝思暮想的土地。 再后来,热扎伊上了大学,选择了她认为最有助于帮助家乡赫尔曼德省的专业——兽医。上学之外,她也会和其他女生一样参加游行,呼吁要平等不要歧视。热扎伊渴望去国外深造,但她坚信,自己最终还是会回到这片土地。因为“每个人的故乡,都是他们的克什米尔。” 而瑞吉娜则是出生在阿富汗,11岁那年跟随父母避难去了美国,几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弗吉尼亚大学。 延伸阅读:《寂静的烽塔》,[阿富汗] 卡伊斯·阿克巴尔·奥马尔 著, 王宝泉、韩佳 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11月。 2001年,美国政府以“9·11”事件为由入侵阿富汗,这个中亚小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也是在这个时候,瑞吉娜感觉到了故乡和人民的召唤。第二年,她持着天真和热烈的理想,与阿富汗民间救助机构签订了工作合同,她计划用6个月的时间改变这里女人的生活方式,“我会让她们明白女性的权利,我会让她们去上学。” 现实却没有想象中容易,几经周折,她在坎大哈建立了绣坊,吸引了当地的女性前去工作,也取得了前期的成功。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离开这里,绣坊的绣品失去了客源,瑞吉娜经营了14年的绣坊只能停业。而她自己,为了女儿,也为了更多阿富汗女童的教育,选择了去喀布尔从事教育事业。 美军进驻阿富汗,以及与塔利班不停歇的战争,让无辜的阿富汗平民在战乱中死去,而阿富汗的女人则在战争中失去了她们的兄弟、父亲、丈夫、儿子。无力如她们,面对这一场场灾祸,只能一次次祈祷,祈祷安拉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让这里重现和平。 “她们希望这个世界知道,阿富汗女人在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和平的渴求。因为她们悲伤地发现,自己国家的男人,无论是政客、商人,还是普通平民,似乎都没有尽最大力去争取它。” 而对另一些女性而言,一次次的轰炸和对女性的种种苛刻束缚变成日复一日的折磨,让她们看不见任何希望,最终只能在绝望中用自己的力量离开。而离开之后的生活又是否会比留下的更好?谁也不知道答案。 动画片《养家之人》(The Breadwinner 2017)剧照。 电影《养家之人》中,帕尔瓦娜与好友肖希娅在最后的告别之际,约定二十年要在月亮拉起海水的地方相见。 如今,二十年已经过去,我们祈愿她们实现了这场期冀已久的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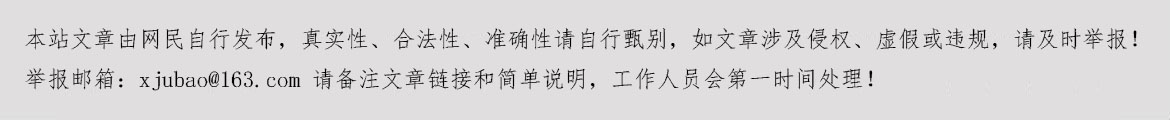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 新闻资讯
• 活动频道
更多




